
这些剧,凭什么能翻红?


独家抢先看


《蜗居》播出十七年了,《我的前半生》也过了九年,这样的时间跨度,足以让两部戏从热播变成旧番,但它们却意外翻红了。“我已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”成为了这两部剧的热门话题。
几乎每隔一阵,就会刷到《蜗居》中海藻摘耳环那场戏,各种翻拍解读,土纯风三个字硬生生被归纳成了一种美学。《我的前半生》更不用说,剧里唐晶那句“我也能养得起你”,在每个讨论国产剧的角落里,依旧被反复提起。


当年看,其实都是别人的故事。
海藻选错男人,活该。罗子君被离婚,可怜。唐晶那么强,是女性的榜样......观众如同阅卷老师,评价三观,指点人生。而这两部剧也像《甄嬛传》一样,从一部作品,慢慢转变成公共素材库,当中桥段被拆开、台词被重估、角色的动机被再次审视,但我们还是不禁疑问,为什么是这两部剧翻红?为什么是现在?
可能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,观众逐渐看懂了。

彼时海藻在车里说的那句“人情债,肉偿了”,当年我们只听到道德沦丧,如今观众依旧批判这种不伦关系,但与此同时却也能体会一个普通女性处于生存焦虑下的无奈。彼时罗子君脱下高跟鞋赤脚踩进积水,当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婚姻失败的狼狈女人,如今却能从其中感受几分坚韧。

女性面临的困境从未消失,现在房子依然捆绑着爱情与安全感,独立女性依然被期待活成某种标准模板,只是多年前我们以为那只是电视剧主角需要面对的问题,如今才明白,生活给了我们同一套考卷,我们只是晚几年进场。
所以重温这些老剧,从来都不是为了怀旧,是想确认,当年让我们愤怒的、鄙夷的、困惑的那些选择,如今再面对,又会怎样看待?

在《蜗居》上映的2009年,其实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,国内房价开始起飞,这部电视剧则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一线城市落户安家的故事。
姐姐海萍与丈夫苏淳,名校毕业,留在上海。他们的家,是租来的十平米石库门亭子间,攒首付,是海萍生活的唯一重心。而妹妹海藻和男友小贝,合租在三居室的一间屋里,计划着存款数字跳到某个节点就结婚。

一切的改变都是从海萍四处筹首付款开始,初入社会的海藻为了帮姐姐减轻压力,最终成了已婚市委秘书宋思明的情人,但海藻面对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两个男人,而是两种生活。
男友小贝代表着简单的爱情,纯粹但易碎,他买得起哈根达斯但买不起上海的一平米,他给的感情很真诚具体,却在一个更庞大的游戏里,被预设了购买力上限。而宋思明带来的是金钱、是权力,他能解决麻烦,能跳过普通人需要遵循的规则,像他说的,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,就不是大问题。

而海藻的堕落,如今也被我们重新检视,现在看她,会觉得愤怒少了,悲凉多了。观众开始注意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:她的动摇与挣扎,并不是因为名牌包,而是看着姐姐和丈夫,被困在狭小的弄堂房,每天为钱争吵,爱情被消耗殆尽,相互之间只剩埋怨,她也看到了一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未来。
一个年轻女孩,在那样原始的生存焦虑面前,手里能握住的筹码如此之少,她的身体与情感成了唯一可快速变现的资产,然而这也正是故事残酷的地方。
海藻并不是那种为了物质入场便能轻松做到只图物质的人,她对宋思明,在依赖与索取之外,也产生了真实的、混杂着崇拜、感激与某种被庇护安全的依恋,她会在深夜等他回家,会因他的关心而雀跃,会认真地纠结于他是否“真的爱她”,她反复对海萍说:“我是真的爱他。”

这句话,当年被当作自我洗脑的笑话,如今再听却透着一种令人心酸的认真。她的悲剧不在于彻底的物质化,在于她的情感,最终无法自控地寄生在了不伦的关系里,让她彻底失去了道义的高地与退路的可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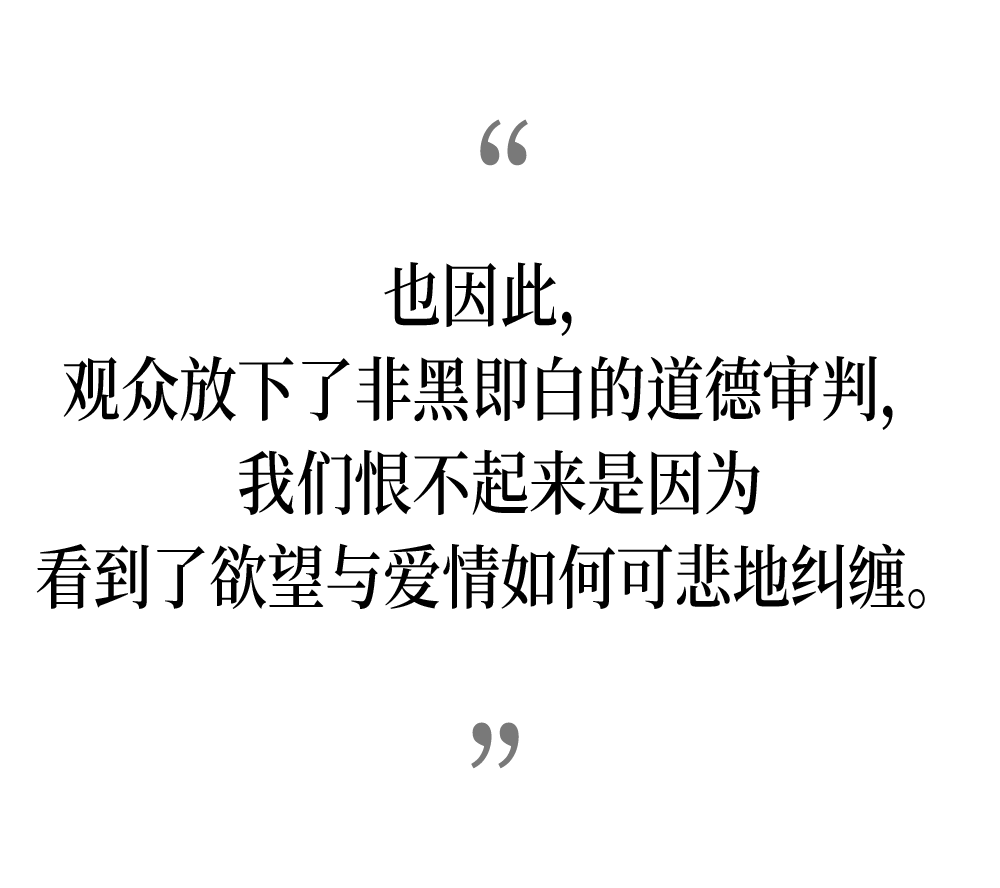
《蜗居》的翻红,是因为它提前十七年,预言了直到今天也存在的困境:在一个被物质、权力与生存焦虑高度结构化的世界里,爱情如何保持它的纯粹性?当情感与交易、真心与计算、依赖与独立早已难分彼此,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一段关系的性质,如何安放自己那颗必然掺杂了诸多现实考量的心?

而当视野拓宽至同期作品,这条爱情观的演变脉络更为清晰,早两年的《奋斗》里,年轻人的痛苦还围绕着理想与自我,爱情作点缀。到了《北京爱情故事》,现实已从背景走到前台,物质开始明目张胆地为爱情标价、分流甚至审判。《蜗居》正处于这个转折点上,它赤裸地展示了,当生存的逻辑全面碾压情感的逻辑时,一个普通人,尤其是一个普通女性的选择与改变。
不过当下,我们却逐渐意识到那道选择题本身,或许就是一个陷阱。


为什么一个女性的安全感和未来,似乎总得通过与某个男性的关系来兑换?为什么“爱情”与“生存”会被放置在天平的两端,且重量从未对等?海藻与宋思明的故事,没有给出答案,只是将这道无解的难题,连同全部的灰色地带,直白地、不加掩饰地,重新又摊开在观众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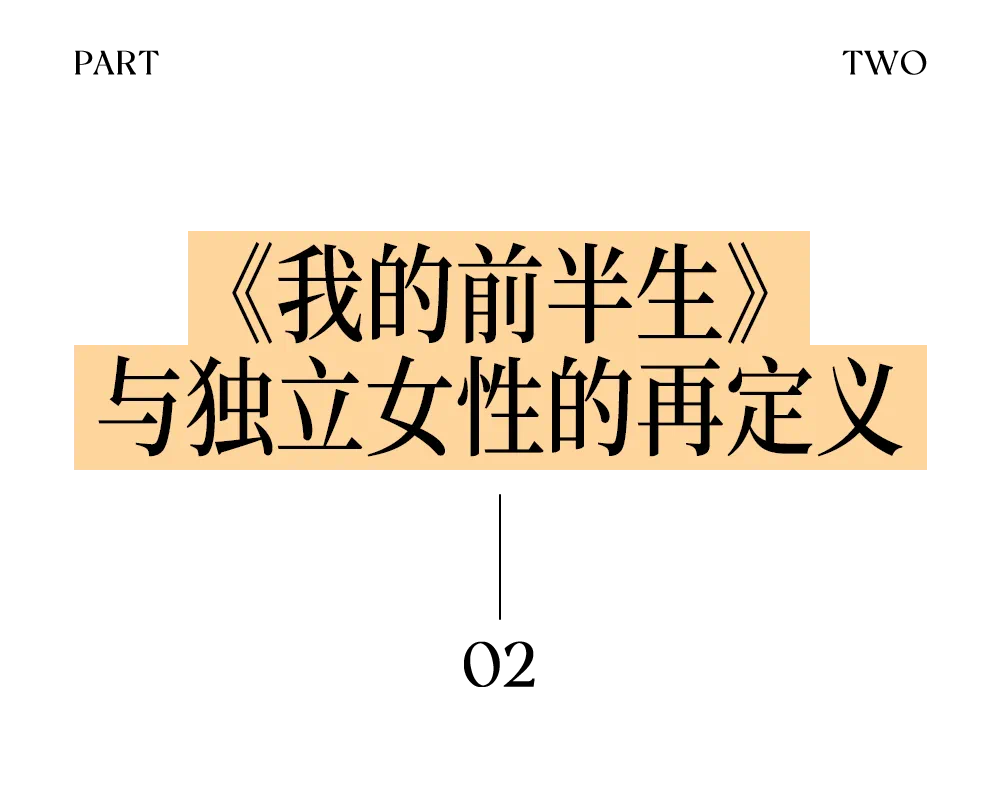
如果说《蜗居》展示了爱情如何在生存压力下异化,那么《我的前半生》翻红,则是对“爱情之后”或“没有爱情之后”女性生存状态的探究,也是一场对独立女性的再定义。
2017年这部剧热播时,唐晶在当时可谓是完美的职场女强人,她穿剪裁利落的Max Mara大衣,对闺蜜罗子君说的那句「他能养得起你,我唐晶也能养得起你」,至今让人记忆犹新,相对而言,罗子君则是一种反面教材,被丈夫抛弃后,竟爱上闺蜜男友,就该受到道德审判。

然而九年时间,评论风向却有了改变。
首先是唐晶,她的独立其实过于严丝合缝,反而成了另一种不自由——她不能示弱,不能出错,她为自己挣到了车子房子,但在发着高烧难以支撑时也会继续工作,即便老板只需要她工作8小时。她的强大,某种程度上是被由男性主导的职场驯化出来的生存方式,无懈可击的理性,本身就是一个精致的牢笼。
而贺涵对唐晶十年的“培养”,也被重新解读为一场漫长的养成游戏。他对罗子君的关注,同样被指出,或许是在另一个“作品”身上,重温创造的快感,爱情退场,权力结构浮出水面。

法国哲学家露西·伊利格瑞曾在《他者女人的窥镜》里讲,现代女性其实长期在男性话语中被定义,进而成为客体。她主张通过「戏拟」,即有意识地模仿男性赋予女性的角色,以过度表演来暴露角色本身的荒谬性,从而解构它,建立真正的主体身份,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——「女人腔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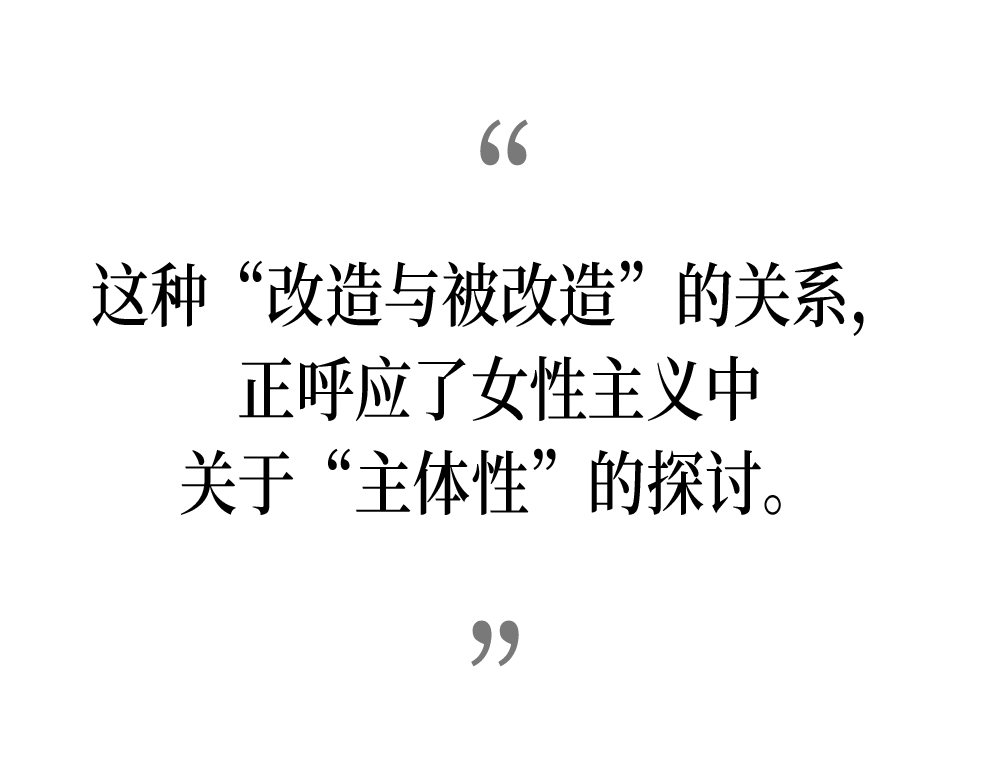
唐晶看似是一名成功的独立女性,她在男性主导的职场里奋力做到了顶尖,但在某种意义上,她仍是卓越的戏拟者,而非规则的制定者。她的处境反而揭示了真正的独立,并不是固定的职业姿态或社会身份,而是拥有从容选择的能力。

这种能力如今甚至可以体现在对主流成功路径的偏离上,就像近年来在瑞典等北欧国家兴起的一股“soft girl”风潮,很多女性开始有意识地拒绝高强度、高压力的职业赛道,转而选择从事创意工作、part-time job,或将更多精力投入家庭,她们并非躺平或退缩,而是以柔和姿态重新定义何为“有意义的生活”与“有价值的劳动”,这种趋势同样延展了我们对于“独立女性”的想象。
与此同时,真正完成逆袭的,反而是罗子君。
罗子君的觉醒,始于主体性的彻底归零——作为“陈俊生太太”的旧身份被注销,但她没有变成唐晶2.0,而是在挣扎中,以一种近乎直觉的方式,摸索属于自己的路。

她跪地为老同学试鞋的屈辱、她对贺涵既依赖又抗拒的纠结、以及最终离开上海的抉择,每一步都充满反复的度量,不符合任何“大女主”爽剧的规范。但这正是伊利格瑞所倡导的,在断裂处生长出异质性经验的过程,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,不是“我应该成为谁”,而是“我可以如何成为自己”,哪怕这个过程笨拙、反复、不完美。
这些都在指引我们想象更立体的现代女性形象,也触及了老剧翻红的核心:观众不再相信完美的叙事。

我们不信海藻能纯粹地物质,于是看到了她的不得已;我们不信唐晶能彻底地理性,于是看到了她的脆弱;我们不信罗子君能简单地逆袭,于是看到了她的挣扎与反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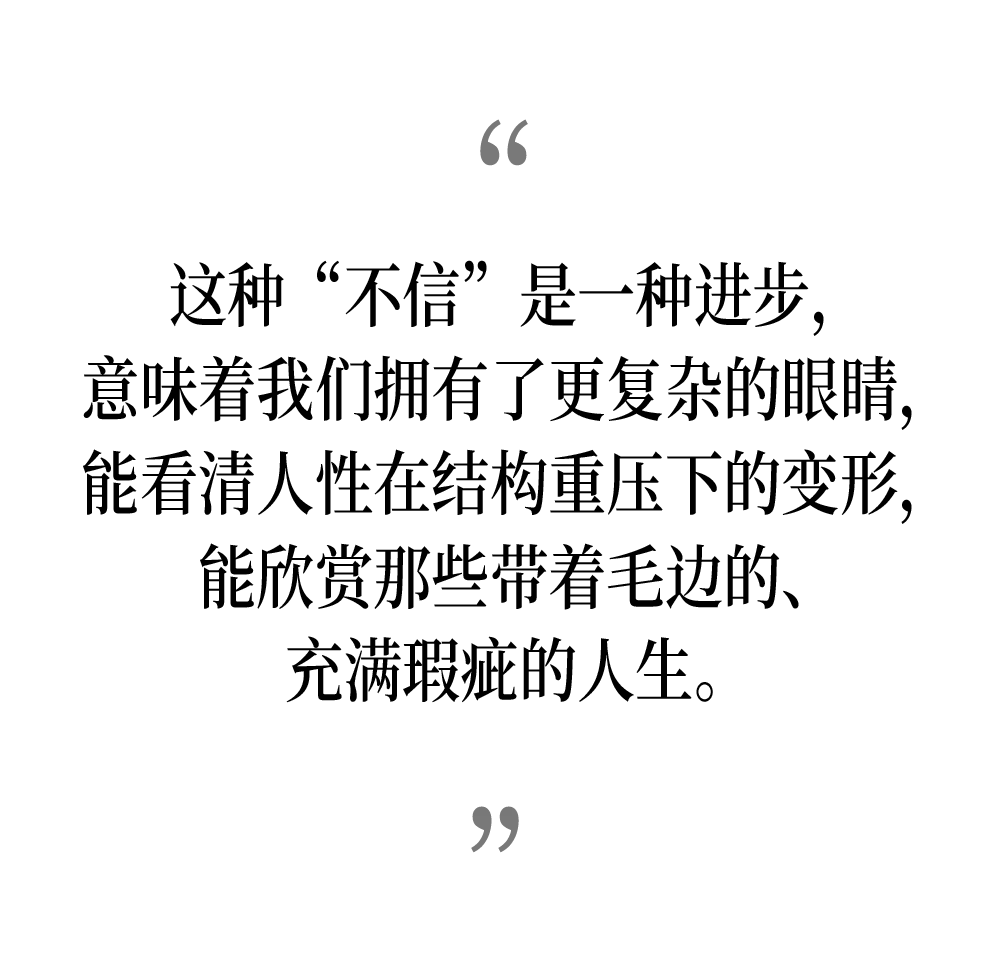
那么,为何是现在?因为此刻,我们依旧处于某种巨大的“中间状态”里,经济从狂热增长进入复杂周期,爱情从浪漫叙事落入现实考量,这些老剧,恰好拥有相似的震荡,回头去看,能找到一些共鸣以及一种确认——我们当下的迷茫,从前也被经历过。这或许就是时间赋予旧故事最重要的意义:不提供答案,但让问题不再孤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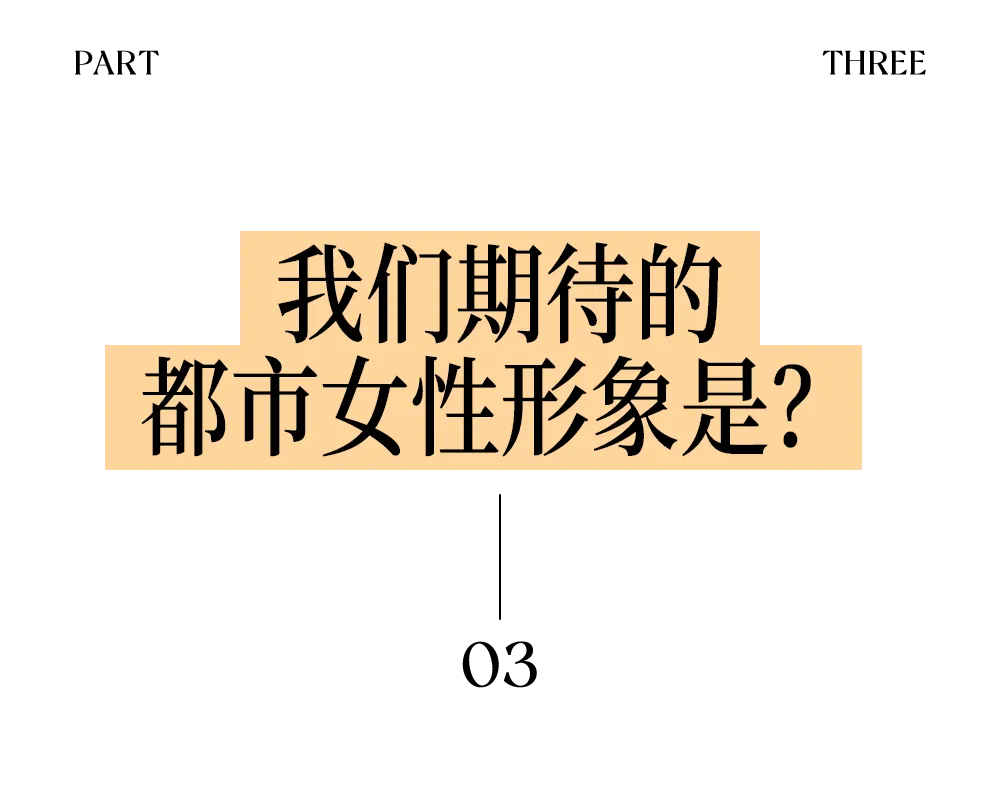
那么,大荧幕如何为我们创造更为立体、更为真实的女性形象呢?
答案是,比起对“女性”标签的简单运用,我们更需要看见复杂而深邃的人性,未来的她,不必是海藻式的牺牲品,也无需复刻唐晶的独立。她首先是一个可以充满内在矛盾、在具体境遇中做出相应选择的人。
而近年来,一些角色已勾勒出这种可能性的轮廓。


比如《繁花》中的玲子,在至真园的推杯换盏间,她的出场依附于爷叔与宝总,但随着黄河路风云变幻,玲子的韧性、市井智慧与最终独自经营夜东京的决断,让她完成了从“他者故事里的注脚”到自我叙事主体的转变。

更进一步的探索,出现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中,李庚希饰演的沈墨,其悲剧的根源固然与男性施加的暴行紧密相连,但剧集并未将她简化为纯粹的受害者符号。她的复仇是沉静的,爱与恨同样坚决,而这部剧的女性从巧云到黄丽茹,她们的形象也都在证明,女性的故事,可以并且应该承载与男性叙事同等的重量。


先前引发热议的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,同样也为我们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女性形象。林依晨与许玮甯饰演的简庆芬与Rebecca,一个看似拥有“标准答案”般婚姻,一个是大龄未婚的单身精英。
故事的焦点不在于评价哪种生活更好,而在于细致地展现两个中年女人共享的困惑、嫉妒、未被满足的欲望与女性之间爱恨交加的情谊,继而启发观众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不能豁免于人生的复杂与遗憾。

而我们所期待的荧屏女性形象,她所追求的“成功”不一定只能来自职场或恋情,也可以是具体的生活,可以源自如何安放自我、与原生家庭和解、在成长中寻求突破......就像许知远说的对微小事物的关切可以超过对宏大叙事的关心。
她的欲望可以复杂,她能同时渴望事业成就、情感慰藉、物质安全与精神自由;她的角色设定,应源于具体的人格与经历,而非“是女性就该如何”的预设;她的人性灰度也可以被确切描述,她能在职场杀伐果决,却在情感中优柔寡断,可以出于利他初衷,却行至自私境地。
最终,归根结底,当我们谈论“不悬浮、有缺点、真实而鲜活”的女性角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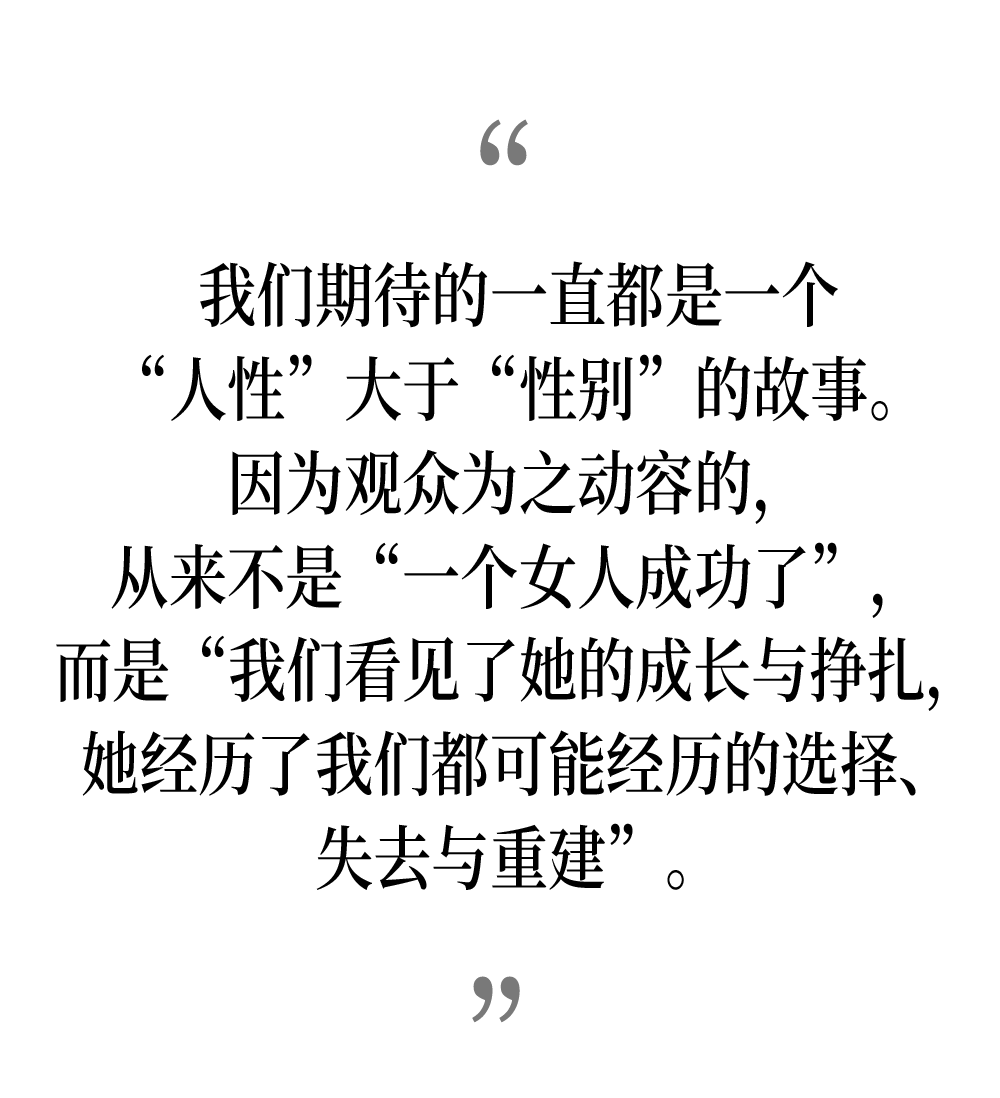

《蜗居》与《我的前半生》的翻红,从来都不是因为观众怀旧,怀旧是向往回不去的时光,而我们不向往2009年高涨的房价,也不向往2017年那个对独立女性只有单一答案的时代。
我们一次次点开老剧,是因为它们拍出了真实生动的女性角色,以及它们所记录的困境从未真正消失,只是换了名字,换了年代,换了一批正在经历的人。






